我們為何要辦一本“自己”的語文刊物
——寫在《文學如何書寫革命——光啟語文教育》出版之際
作者: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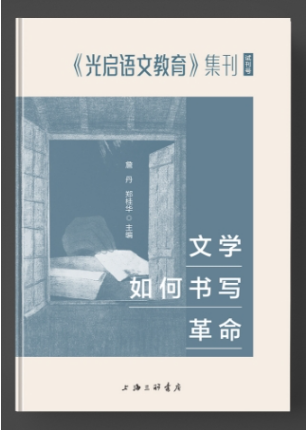
編一本自己的刊物,是我和鄭桂華老師一直念叨的。
我和她都自許為語文人,同在上海師范大學,依托光啟國際學者中心的平臺成立了語文研究院,辦刊物就提到了議事日程。這是要為我們語文人忙碌的工作留下一點印跡,讓我們、我們周邊人的工作和想法被更大范圍的人看見。我們也有一個小心愿,就是為了讓我們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可以隨心所欲一些,而不必受許多雜志要求的發表規范或者書寫格式乃至篇幅長短的束縛。盡管這樣或那樣的要求也確曾為語文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因此而滋生的形式主義或者教條主義流弊,也正在抑制著我們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的發揮。
同時,辦一本語文教育類刊物,也是為了讓高校學者和中小學語文教師,有在同一個平臺交流的機會。
我們深知,高校學者有關語文教育的理論研究和一線語文教師的實踐探索,都埋頭苦干了許多年,積累下不少成果,但彼此間又似乎是老死不相往來的,似乎各自站在兩根難以相交的平行線上往前邁開自己的步伐,只是偶爾才會側頭互相觀望一下。伴隨著這種狀況,我們固然看到了,一方面高校的專家學者潛心于自己的理論研究,對語文教育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對新課標的核心概念和新教材實施,提出了不少高屋建瓴的看法;另一方面,一線語文教師以他們基礎教育的實踐經驗取得的收獲,使語文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越來越擺脫個人即興式的隨機發揮,而日益回歸理性、回歸語文教育規律的探索中。但是,大學和中小學、專家和一線語文教師、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那種研究和教學地自覺區別站隊,使得彼此間的隔閡亟待彌合。
毋庸回避的問題是,有些專家學者對語文教育的現狀關注不夠,對一線語文教師的內心訴求了解不透,對真正制約學生成長的因素把握不準,或者說,過于抽象、宏觀地把握現實而提出的一些高大上理論,因其高蹈、玄虛,而只能在理論自身的邏輯框架內打轉,無法真正應對現實,解決語文教育的實際問題。與此同時,部分一線語文教師以專家學者的研究不適合基礎教育學情為由,或者以某些出現偏差、失誤的理論為說辭,拒絕一般意義的知識學習和理論更新,使得他們的思想觀念,越發趨于陳舊和僵化,而沒有思想更新帶來的活力,讓他們的教學實踐也變得視野狹窄,格局逼仄。
我和鄭桂華老師相似,都有過當中學教師的經歷(盡管鄭桂華深耕課堂的經驗比我遠為豐富),后來又來到高校執教并開展研究工作,所以深切地感受到,打破語文研究界和基礎教育界的藩籬,讓大學研究者和中小學教師在同一個平臺對話、交流,讓理論得到提升,讓經驗得以總結,讓教訓獲得反思,讓語文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形成有機融合,正是我們創辦這樣一本刊物的宗旨。
國內語文教育類的刊物已有許多,創辦《光啟語文教育》集刊,不是在這“多”中簡單地加上“1”,而是想努力辦出自己的特色,讓這個“1”能顯得與眾不同。一個初步的想法是,既然這本刊物,在作者和讀者方面,努力打破了大學和中小學的壁壘,那么在來稿的內容和形式上,也應該持開放心態,不必太強調話題的整齊劃一和行文的格式規范。比如,對一些似乎過于口語化的演講稿和評課實錄,也沒有要求作者削足適履地來修改成八股式的論文體,才同意發表(我還記得,我的一篇教學現場點評實錄因其行文的口語化而曾被某刊物要求改寫成書面化語言,我試著修改了幾段,卻覺得自己的想法正在被自己一點點閹割時,最終默默從雜志撤回了稿件)。只要言之有物,確實提出了益人心智的見解,都是值得發表的。
在欄目的設計中,給予了文本解讀以特別的關注。我始終認為,當好一名語文教師,文本解讀是其基本功(想當年,我在嘉定實驗中學剛任教初中語文,時任校長的錢夢龍就是這么教誨的),教師缺少文本解讀的功力,常常自己把文章給讀歪了、讀偏了,那么很高明的教學設計,只能造成南轅北轍的效果。刊物也歡迎好的教學設計和教學實錄,所謂好,并不預設標準,不會認為在課堂上,組織學生的發現學習就一定優于接受學習,只要能在單位時間里讓學生更大受益的教學,就是更好的教學。就如同在沒有接觸到具體教學案例時,編者不會在單篇教學和單元教學間下一個孰優孰劣的判斷。此外,有關新課標的、新教材的、測評的、教育名家研究的好文章,刊物也十分歡迎。
我們期待,在未來,《光啟語文教育》不但要成為語文人向往的交流平臺,也是語文人的精神家園。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光啟語文研究院)
鏈接地址:https://share.gmw.cn/wenyi/2024-12/26/content_37769603.htm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
徐匯校區:上海市徐匯區桂林路100號